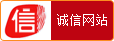拓展大运河商业文化史研究
大运河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条黄金水道,它极大带动了沿岸区域物资交流和商业流通的繁荣。与之相伴,运河税收日益增多,构成了古代王朝重要的税收来源。大运河的畅通,使沿岸区域逐渐形成了以大运河为商品流通主干线的城乡市场网络。大运河商业文化,就是经由大运河及其辐射区域内进行商业活动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化现象。从漕运与商业的关系入手研究大运河商业文化,能够凸显贡赋体制与商业资本间的互动关系。以往关于大运河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漕运史和运河区域社会史,而若要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整体性研究,大运河商业文化将是一个很好的契合点。
元朝对前朝河道采用“弃弓走弦”、截弯取直的方法予以改造,形成了京杭大运河的骨架雏形。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逐渐成为漕运和商业水运的主干线。漕运与京杭大运河商业贸易的特殊关系,大运河商业文化的历史逻辑,以及围绕京杭大运河商业文化所形成的江南、淮扬、黄运(黄河与大运河交汇地带)、华北等几个特定区域,是大运河商业文化史研究所面对的主要区域和领域。
就商业文化史研究而言,已有许多学者作出了不少值得关注的探索。加拿大学者卜正民沿着从交通到商业、从商业到文化的轨迹,探讨明代商业及其社会影响的意义,交通系统的改进使得商品流通变得更为便捷,并形成官僚等级体系与商业贸易相结合的特定商业文化。美国学者曾小萍提供了一个内生型商业实践的案例,在某些边缘地带以商业传统著称的地方,商人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利用契约传统、亲属关系、商业习惯等,去挖掘尚待开发的资源,并组建合作商业组织、进行制度建设,其中“商人伦理”的作用需要认真审视。此外,古代商业实践中形成的“伙计制”等一些新的制度创新,联结上层文化和通俗文化的绅商,恰好为儒家思想转化为商业伦理提供了某种可能性。同时亦可看到,在明清商业实践与制度演进中,即使发生如科大卫所说的“商业革命”,固有的观念、民俗和行为方式始终是一种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存在,呈现了坚韧的历史延续性。可见,所谓商业文化,包括商人伦理、商事习惯、契约传统、商业民俗信仰等一整套文化模式。
运河商业文化更带有其特定的历史、地理、区域社会文化特征,其主要表现就是运河商业文化与漕运不可分割的制度性联系。对漕运史的研究也充分揭示了这一点。日本学者星斌夫关于明代漕运的研究表明,官吏从私商手中购买稻米以弥补漕粮定额,造成了漕粮的逐渐商品化。黄仁宇也阐明了明代漕运与大运河商业文化之间的关系,认为漕河上的商品运输以北方为主要去向,因为北方主要是买方,而南方则主要是卖方,所以这种贸易是不平衡的。李文治、江太新发现,道光后漕运改制,漕粮海运比例增加,再加上黄河改道、京畿食粮通过商品粮运输得到部分解决等因素,大运河漕运和商业贸易的关系发生了很大改变。
京杭大运河每段河道并不具备共同的特点,而且其与自然河道不可避免地存在交汇连接,这为不同区域与大运河的互动留下了地方性实践的空间。不同的运河区域,其商业文化的形态也有所不同。比如,王振忠的研究显示,徽商在淮扬地区的聚集,促进了当地商业的发展,形成了团、场、坝、市、镇等多层次的市镇类型;而许檀对华北地区运河城市的商业规模、市场网络以及市场层级作了详细分析,指出一批商业市镇尤其是设有税关的商业城镇,成为以中转批发贸易为主的流通枢纽城市。
以上三个方面的研究都突出了商业文化对于京杭大运河历史研究的意义,从不同角度关注了漕运与商业文化密不可分的联系。在此基础上,如果要拓展京杭大运河商业文化史研究,还需将漕运史、商业文化史和区域社会史结合起来,进行整体史的研究。
以漕运与商业文化的关系为主线,来阐述大运河商业文化中的贡赋体制与“商业资本”的互动关系。为此,可从贡赋体制下商人依附性和反抗性群体性格的矛盾统一面相,探索商业实践过程中商帮制度伦理的形成。以大运河串联起来的众多商业市镇为线索,探讨它们的形成过程、发展历程与商业功能。运河钞关是国家与地方的税收机构,其所征税种、税额的不同表明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可从商业史角度分析商品流通、构成、消费等情况。商业民俗是大运河民俗文化的精华所在,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涉及与商事活动有关的民俗现象,如刘猛将、金龙四大王等运河商业神明崇拜,牵涉到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运河区域社会一体化的黏合剂。
将商业文化纳入大运河区域社会史视野下。在美国学者施坚雅“区系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探讨其区系空间体系,即由区系论可以解释区域市场体系的社会逻辑,即市镇作为中间结构,连接了贡赋体制与市场,整合了税收、军事防卫与地区商业供求关系,最终将市场体系与运河商业民俗“信仰圈”等结合起来,从而进行整体史的研究。大部分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和经济人类学的学者,都将施坚雅的基层市场体系和区系论的理论取向,划为经济人类学中的形式主义学派,认为其基本的理论前提是经济人理性最大化假设,笔者认为其实不然。且不说施坚雅没有参与经济人类学中的形式主义和实质主义的论争探讨,单就基层市场体系和区系理论本身而言,实际上是对中国社会的某种实质论分析。基层市场体系不仅仅是一个贸易体系,还是一个社会体系、市场社区,举凡行会、秘密会社、庙会、宗族等组织,均在市场社区空间中活动。区系理论,则在研究单位上突破了行政区划的窠臼,且探讨了官府治所设置和贸易体系、赋税征收的关系,即封建王朝在容许商人通过长途贸易逐利的同时,还通过贡赋制在总体上榨取农业剩余和商业利润。
将“大运河商业文化”作为一个富有解释意义的概念,不仅能够凸显刘志伟所说的“贡赋经济”对王朝国家的意义,还能发掘民间商业资本的贡献,更有助于全面地对中国社会经济史作出整体解释。比如美国人类学家葛希芝的“二重生产方式”理论,即贡赋式生产方式和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是通过亲属关系,通过阶层间的人际关系,通过把贡赋生产方式的准则强加在私人关系上以及在公众关系中掺入市场准则的意识,还通过两种生产方式在同一生产者范围中的共同基础而联结起来,并且时常处于矛盾的状态中。这一概念可以很好地解释绅商既依附官府又追求商业利益的矛盾性格,有助于解决商人伦理无法超越官府控制与民众自治时代矛盾的问题。
我们希望,未来对大运河商业文化史的研究,可以立足中国本土实践,彻底突破“西方中心论”藩篱,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构建新的运河文化和运河区域社会史的解释体系,塑造更有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意义的史学研究话语体系。
《光明日报》( 2021年10月04日 06版)
作者:张佩国 周嘉(分别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长聘教授、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副教授)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7341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734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