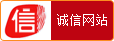千年运河贯穿古今 江南文脉奔涌不息
大运河,上下2500余年,绵延3000多公里,流经中国版图的8个省市,是世界文化遗产,更是中华文明的标志。清波一脉通古今,开凿于先秦时期的江南运河,作为中国大运河的组成部分之一,将江南的各个城市如明珠般串联起来。大运河带来的是城市发展的滋味源头,是城市腾飞的汩汩清流,它带来了江南的千载繁华,见证了江南城市的兴替更迭。时至今日,江南运河始终是京杭运河运输最繁忙的航道,在区域经济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
繁盛社会经济的源头活水
江南运河与长江、江南自然水网所共同形成的资源优势,是江南社会经济繁盛的源头活水。江南运河,北起江苏镇江,绕太湖东岸经常州、无锡、苏州,南至浙江杭州,贯穿长江、太湖和钱塘江三大河湖水系,同时,又通过吴淞江、太浦河连接上海。从经济学角度讲,所有运输当中,水运是最便捷且便宜的。自春秋战国以来,江南运河与天然的江河湖海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水网,形成了四通八达的水运交通网络,奠定了水乡泽国的自然与人文生态。隋朝开始开挖疏浚的江南运河,被纳入到全国统一的漕运体系,是众多江南地区运河中最主要的漕运水道。
在长三角地区,江南运河与长江一起,一横一纵拉开了整个江南地区最重要的水系骨架,它与长江共同成为江南水运交通网络的两条主干线,同时,又与江南自然水网一起共同构成了影响江南社会经济文化繁盛的源头活水。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曾说过:“隋唐时期交通相当发达,运河和长江的水上交通尤为当时后世所称道。运河有不同的渠道,渠道相互连缀,可以通到许多地方。”
以三江之一的吴淞江为例,《尚书·禹贡》有“三江既入,震泽底定”的记载。吴淞江的别称“松江”,其实就是现在上海地区古代行政建置“松江府”的命名来源。吴淞江下游近海处被称为“沪渎”,是上海市简称的命名来源。据资料记载,吴淞江(苏州河)上海段是上海近代最早的工业区,民国年间有修造船、面粉、棉纺织、丝织、化工、冶金机械,甚至水电煤器具的加工厂,在苏州河岸线,集中了数以千计的工厂,其中的纺织厂、面粉厂、火柴厂、钢铁厂、造币厂、啤酒厂、无线电厂、制药厂、石油化工机械设备厂等,都曾在上海乃至全国工业经济史上创下纪录。
以苏州为例,苏州有“水韵古城”之称,其“水陆双棋盘”的城市格局一直延续至今。“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水城的格局,是由以太湖为源头和大运河为骨干的江南水系将星罗棋布的湖泊河荡和纵横交错的水巷河道连成一片,从而形成的一片举世无双的水乡世界。黄金水道的运河水系、水乡古镇的风貌水系、三横四直的城内水系以及逐水而建的园林水系,各类水系结构交相辉映,融汇合璧,形成了一组世界上罕见的东方水城风貌图。而依靠这样的水网系统,苏州成为历史上南来北往人员、物流的重要集散地和中枢地。借助大运河,漕运和海运在苏州形成了彼此呼应的联动效应,为南北物资平衡与往来、塑形全国统一性的社会与市场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孕育江南文化的丰沃土壤
大运河,尤其是江南运河的畅达,为江南文化的发展孕育了丰沃的土壤。江南是一个依水而生、依水而兴的地方,大运河滋养了江南的经济发展。在历史长河的绝大多数时期,江南运河沿线受战争袭扰相对较少,随着“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乱”后的三次南迁,江南地域的人口快速增长。据史书记载,“平江、常、润、湖、杭、明、越,号为士大夫渊薮,天下贤俊多避地于此”。同时,发达的水运又催生了商业文明的萌芽与发展,南北经济文化的频繁交流,使江南沿运河地区长期成为古代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苏州更是在明清时期一度成为江南乃至全国文化中心地带。朝鲜人崔溥在其《漂海录》中有一段话:“苏州古称吴会,东濒于海,控三江,带五湖,沃野千里,士夫渊薮。海陆珍宝,若纱罗绫缎、金银珠玉,百工技艺、富商大贾,皆萃于此。自古天下以江南为佳丽地,而江南之中以苏杭为第一州。此城尤最。……阊门码头之间,楚商闽舶,辐辏云集。又湖山明媚,景致万状。”
清代宫廷画家徐扬用了24年时间画了一幅全长1225厘米,比《清明上河图》还要长一倍的画卷,取名为《盛世滋生图》,后改名为《姑苏繁华图》。画面自灵岩山起,由木渎镇东行,过横山,渡石湖,历上方山,介狮和两山间,入姑苏郡城,经葑、盘、胥三门出阊门,转山塘街,至虎丘山止,画笔所至,连绵数十里的湖光山色、水乡田园、村镇城池、社会风情跃然纸上,被称为研究250年前“乾隆盛世”的形象资料。这幅画是研究江南运河和江南文化最好的资料之一,但其本身,也是江南文化最好的表达之一。
根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统计,明清两朝全国录取进士51681人,其中明代为24866人,清代为26815人。江南共考取进士7877人,占全国15.24%,其中明代为3864人,占全国15.54%,清代为4013人,占全国14.95%。总体而言,明清两代每7个进士,就有一个出自江南。
英国文化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了“狭义文化”的早期经典学说,即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江南文化,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其文化门类繁多,文化内涵深远,文化质量高超,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超越了文化本身而存在于所有向往精致、典雅、宜居、诗性生活的国人的心里。
明清时期的人,凡是有一定文化的,中过举的,做过官的,可以说没有不经过运河的,运河“是联结中国南北、贯通中国与世界,集中展现明清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里程的人类宝贵遗产”。
传播江南文化的不竭动力
江南运河的流通,为江南文化的输出与交融畅通了渠道,是江南文化传播不竭的动力源泉。事实上,大运河全线贯通后,不但成为南方漕粮北上的输送线,而且成为南北之间商品往来、人文交流的最大通道。其实,作为古代中国的交通大动脉,大运河上文化的南来北往从未停止过。如翁俊雄先生说:“德宗兴元以后,汴河复通。此后,南来北往的旅客,多经此路。”
不止是唐宋,在明清时期,江南经济与文化获得更高层次的发展,大运河的交通枢纽意义也变得更加重要。
以昆曲为例,嘉靖年间昆曲兴起后,到明末“今京师所尚戏曲,一以昆腔为贵”,一时间竟出现了“多少北京人,乱学姑苏语”的盛况。明末徐树丕说:“四方歌曲,必宗吴门,不惜千里重资致之,以教其伶伎。然终不及吴人远甚。”
以昆曲为代表的江南文化的北上传播中,运河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除此以外,苏样、苏意、苏酒、吴馔、苏作等也通过运河传播至全国各地,以致明代万历年间的王士性说:“姑苏人聪慧好古……又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又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尚古朴不尚雕镂,即物有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亦嘉隆万三朝为盛。”不仅如此,这些江南的物件以及引领的潮流甚至于一度因其魅力而流传至日本、朝鲜、琉球和西欧各国,如姚士麟曾援引中国商人童华的话说:“大抵日本所需,皆产自中国,如室必布席,杭之长安织也;妇女须脂粉,扇漆诸工须金银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饶之磁器,湖之丝绵,漳之纱绢,松之棉布,尤为彼国所重。”
而因为有了运河,江南文化北上之路畅通,中原地区的士大夫则因为仰慕、追捧江南文化而纷纷南下。戏剧大家孔尚任在《郭匡山广陵赠言序》中写到:“天下有五大都会,为士大夫必游地,曰燕台、曰金陵、曰维扬、曰吴门、曰武林。”其中三个是运河城市,而且集中在江浙两省。这一来一往,文化交流、融合的良好动线便形成,在文化的南北交融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融汇贯通。
1843年,上海正式开埠。国外势力进入,开辟租界,获得了沿海和长江的航运权,带来了工业化的因素。江苏省社科院王健教授论述:“上海的崛起,标志着中国的经济重心区域由‘运河时代’走向‘江海时代’。”其实,运河时代也好,江海时代也好,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自始至终都是地缘相接、同根同源的。应该说,自宋以来的杭州,到明清时候的苏州,到民国以来的上海,再到现代的长三角一体化城市群,江南文化的城市表达在千年运河的起落中呈现。上海社科院原副院长、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熊月之对此有精辟的论述:“在宋代‘城市革命’的大背景下,江南的城市逐渐取代了原来农村的文化功能,尤其伴随着明清以来大量乡间士绅移居城镇,江南文化最精华的部分都已经转向城市和城镇之中。近代的海派文化也是直接继承自江南的城市文化。”
因此,新时代,对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江南文化品牌的打造、“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与长三角一体化、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战略的协同发展问题,擦亮中国大运河的金字招牌,以国际化的视野做大做强“江南文化”品牌,不仅是薪火相传活化千年文化资源资产的需要,更将是面向未来增强文化自信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
陈璇(作者系苏州市职业大学石湖智库副秘书长、教授,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副院长。)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7341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734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