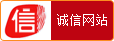古时大运河与通州“抗疫”

清末民初通州燃灯塔旧影
通州位于京杭大运河北端,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因此在历史上有关瘟疫的记载也占有一定的篇幅。比如《通州志》记:“万历十年(1582)春,通州大疫,比屋传染,虽至亲不敢问吊。”连至亲都不敢去探望,由此可见这次瘟疫的“惨烈”。
翻阅史书可以发现,大凡通州地方志书所记载的瘟疫,北京志书中也有相关记录,而北京志书中记载的内容,也往往会提到通州。比如《通州志》记载了一次瘟疫,“崇祯十六年(1643)七月大疫,名曰疙瘩病,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
这次名为“疙瘩病”的瘟疫,是明末史料中常见的瘟疫,而且危害非常大。根据研究,“疙瘩”是对腺鼠疫患者淋巴结肿大的称呼,患者的身体肢节间会突生一个“小瘰”,接着“饮食不进,目眩作热”,只要一人被感染,全家都会被传染。
在史料中,崇祯十三年、崇祯十四年都有疙瘩病的记载。每次出现这种烈性传染病时,“人死十之八九”。当时李自成的起义军里也出现了“疙瘩病”,时人记载:“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或一家数人并死。”
因为传染性强,崇祯十六年通州所记的“疙瘩病”,不可避免地也出现在昌平、河间等地方志书。
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十九年(1680)记载了一次瘟疫,“自春至夏,通州无雨,瘟疫大行”(康熙版《通州志》),而同样是康熙十九年,《清史稿》记载了苏州的一次瘟疫:“正月,苏州大疫。”一个是北方的通州,一个是南方的苏州,虽然相隔千里,却在同一年发生了瘟疫。这次相隔千里的疫情或许存在某种关联:大运河。
为何这么说?翻开中国历史不难发现,在关于瘟疫的记录中,瘟疫发生最多的地方,并不是人们想当然以为的自然条件恶劣的边鄙烟瘴之地,反而是人口流动最多的繁华地界。
元、明以来有瘟疫历史记录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发生瘟疫最多的城市,多是在京杭大运河沿线城市,这些地方人员流动密集,人口规模巨大。
通州是京杭大运河的北端码头,各地供给京城的物资以及随行人员、商贾等,几乎都要在通州中转,因此,如果一地发生瘟疫,传到通州的可能性极大。比如康熙十九年的那场瘟疫,从时间上来看,苏州是正月发生瘟疫,通州在春夏之交便发生了瘟疫,虽然并没详细的史料说明通州的瘟疫来自苏州,但这两处疫情的地点和时间,的确因为大运河有了某种关联。
再有《民国通州志要》记载,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通州霍乱流行”,当时的《大公报》记这次霍乱“始发于塘沽”,可见这场瘟疫是由天津传到通州的,虽然此时大运河的漕运已经几乎废弃,但因通州与天津的距离非常近,且通州仍是中转之地,也因而被传染。
那么中国古代是怎样防控瘟疫传播的呢?古代称瘟疫防控为“降疫”,所采取的手段居然和今天相差无几:那就是隔离。针对疫情传染的特性,阻断反应几乎是下意识的。《汉书·平帝纪》记载,汉朝对待瘟疫采取防控措施,便是“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也就是专门腾出空房来隔离,在相对空旷处临时设置“疠人坊”,这是中国针对瘟疫采取“隔离”措施的最早记载,后世历代沿袭。
采取隔离措施之后,就是对病患的救治和环境整治。比如《析津志》记载:金朝海陵王筑金中都,因时逢夏季暑热,人多劳苦生活条件又很差,最终导致瘟疫暴发。当时的海陵王是怎么处置的呢?《金史·张浩传》记:“诏发燕京五百里内医者,使治疗,官给药物。全活多者与官,其次给赏,下者转运司举察以闻。”也就是说,发生瘟疫时征调各地“医户”支援疫区,而且还根据救治效果给予赏赐。
古代的医学没有现代发达,但古人也直观感知到了环境整治对“降疫”的作用,那时人们认为引发瘟疫的主要是“瘴气”,而瘴气的根源则在水源,以古代北京地区为例,每遇瘟疫流行,便对“井窝子”(卖水的水铺)特别管制,对吃用水井加封井盖,为防止老鼠及其“病瘤”(即病毒或病菌)落入,同时还要清理城中沟渠,及时排泄城中滞留的脏水。这些办法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病毒或病菌的传播。
作为京畿重地且人流密集的通州又是怎样面对瘟疫的呢?在瘟疫的预防监测上也比其他地方更多程序,清朝刊行的《海录》中规定,海外船只进入中国港口要接受检验检疫,“凡有海艘回国,及各国船到本国,必先遣人查看有无出痘疮者,若有则不许入口,须待痘疮平愈,方得进港内。”这还是海外船只进入港口,再通过运河登岸通州,检验检疫也会更加严格。
通州作为京杭大运河漕运北端码头,历史上在对抗瘟疫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今,通州迎来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新时代,通州地区的人口流动更多,城市规模也会越来越大,这将为通州带来空前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带来了某些风险,通州,准备好了么?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7341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7341号